《惶然录》:写下就是永恒
来源:文艺报 | 孔戈碧 2018年06月27日08:1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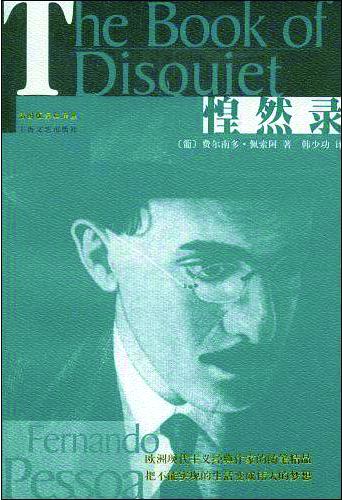
“有时候,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。一旦写下这句话。它对于我来说,就如同永恒的谶言。”读到开头这句话的时候,我完全被震撼住了,我无法描述出那一刻心中的感受。因为佩索阿写下了永恒。
费尔南多·佩索阿1888年6月生于葡萄牙里斯本,父亲在他不满6岁时病逝,从1908年起,佩索阿一直独自一人生活。除此之外,他就如卡夫卡一样,只是里斯本一个公司的小职员,整天默默工作,从来不多说一句话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:“我从来不求被他人理解。被理解类似于自我卖淫。”但卡夫卡对于周围环境的敏感,总是令人为之不安。而佩索阿一生乐于充当一名公司小职员,他安于自己小小的社会角色,始终坚定不移地固守自己的写字桌,就像一直远航的船只渴念码头。“我走近我的写字台,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。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。”这种不可阻挡的温柔,使他有别于卡夫卡。温柔是对世界的软化,对工业时代、战争、专制、粗糙的生活,对一切坚硬事物的最决绝的反抗。因此他对待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上司时,感觉到“我的某一部分将与他们共存,失去他们的我将与死无异”。“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,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”。无论能否成为V公司的主管会计,还是在临终前写下“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带来些什么”,除了能够写作,他知道自己和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他的灵魂从来没有停止过骚动,虽然他并不觉得思考是多么高贵的事,但他相信:“思考比生存更好,这是我的不幸,与其他所有的大不幸随行。”他注定是孤独的,因为他的思考就如同西西弗斯,永远向前而又返身自看,自我始终在镜像中凝视。他的感知,来自于敏锐的洞察。他以令人羡慕的耐力向内勘探,黑暗之心如同一个回声阵阵的深渊,通过收集回声他树立起一座内心的金字塔,这是一座“自我意识”的宏大塔楼,它与外在的宇宙构成了一种诙谐的、颠倒的关系——意识之微的体察往往能放大成占据整个虚无空间的冥想。我们越是解剖自己,越是将个体的感觉一一供示出来,我们对“世界”的依靠程度也就越低。那无限的向内、向内、再向内的倾斜,让整个世界在这一道像大地一样空旷的斜坡上变得轻盈、透明、可以理解;即使仍不可理解,至少也与我们达成一种柔和的谅解。
佩索阿平素极少出门,甚至在17岁以后的30年里几乎没离开过里斯本。他或许是除康德以外最讨厌旅行的人,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之外,连里斯本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很少去过。佩索阿认为,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旅行。“世界的终点以及世界的起点,只不过是我们有关世界的概念。仅仅是在我们的內心里,景观才成其为景观。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。我们看到的,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,而是我们自己。”在这个意义上他也称自己为静止的旅行者和“第八大洲”的旅行者:“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沒有兴趣,也沒有真正去看过。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。有些人航游了每一个大洋,但很少航游他自己的单调。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。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。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。我渡过的大河在一个不可能的世界里奔流不息,在我沉思的凝视下确凿无疑地奔流。如果旅行的话,我只能找到一个模糊不清的复制品,它复制着我无须旅行就已经看见了的东西。”的确,我们不必再为自己沒有去过什么地方而感到惶恐不安,最重要的,乃是拥有广阔而丰富的內心世界。记得很早以前读《老子》中的那句“不出户,知天下;不窥牖,见天道。其出弥远,其知弥少”总觉难以理解,如今读到佩氏此语,顿觉豁然开朗。一个拥有着丰富内心的人对于外界的依赖最少,因此也是最为完满自足的。他以卑微之躯处蜗居之室,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,始终一贯地保持了对于一切事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。
佩索阿的生活单调规律,每天准时上下班,对于这种单调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,佩索阿在日记中有所描述:“聪明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,以便使最小的事故都富有伟大的意义。……哪里有新奇,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,而后者总是毁灭了前者。真正的聪明人,都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的壮景,无须同任何人说话,无须了解任何阅读的方法,他仅仅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五种感官,还有一颗灵魂里纯真的悲哀。”毫无疑问,佩索阿的灵魂里正好有这种纯真的悲哀,因而他躺在里斯本这张躺椅上就可以欣赏整个世界,而且顺便将这个世界贮藏在文字中。整部随笔都像在他写作的间歇——当他写累了,在深夜停下笔来,看着窗外寂静的街道,想起了白天见到的一些人和场景,虽然普通,但在这样的深夜,在人的思维的深夜,它们似乎也突然具备了伟大的意义。对于他本人而言,写作是对于自己内心的一次访问,以飘浮的语词刻画出内心真实的喜悦与忧郁,悸动与不安交织的交响乐。
在这本书中,你可以看到佩索阿有意识地分裂自己,变换另一种视角,以他者的身份和视角介入写作;随后,他又以自省的态度站在一边检阅自己的作品;他获得了更多地体验生活的机会。孤独使他创造出许多想象中的伙伴,那些变中的恒,异中的同,让他在不同的角色中穿梭自如。他的立场时有转换,有时精神化有时物质化,有时个人化有时社会化,有时贵族化有时平民化,有时科学化有时信仰化,“一直在心灵中自我否定”。但正如韩少功在译序里所言,较之执著定规,他的自相矛盾常常是智者的犹疑;较之滔滔确论,他的不知所云常常是诚者的审慎。这是变中有恒,异中有同,是自相矛盾中的坚定,是不知所云中的明确。这恒与同、坚定与明确,就是独自一人面向全世界顽强突围的精神气质!
佩索阿生在革命的年代,死于独裁年代,但是这个羞怯而忧郁的外交官继子并不关心时代的洪流。他厌恶他的时代,同时也是一个极度厌恶政治的人:“对世界的统治始于我们对自己的统治。统治世界的既不是忠诚,也不是不忠诚。统治者是这样一些人,他们以造作和不由自主的方式,在自己身上制造出一种真正的忠诚;这种忠诚构成他们的力量,闪闪发光,使其他人的虚假忠诚黯然失色。一种自我欺骗的杰出天才,是政治家们最起码的素质。”——这里对政治的鄙薄不言自明,比那些从正面抨击政治之肮脏的做法还要入木三分。他反对一切暴力,视其为“人类愚笨品质特有的疯癫的特例”,这是无数血淋淋的生命证明的历史真相。他的目光深入黑暗的核心:“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,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,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早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,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,他将要发现,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。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。”这是他对革命和改良的思考。
作为一个诗人,佩索阿的文字特别典雅、精准、洁净,充满了诗性之美和智性之美,体现了对思想对生活一种智慧的悟力,穿透了尘世和自然。比如:“纯粹,就是不要一心想成为高贵或者强大的人,而是成为自己”、“一个人只能看见他已经看见过的东西”、“我们把生活想象成什么样,它就是什么样。生活全看我们是如何把它造就”、“秋天不是在世界里而是在我们内心中开始”等等。书中这些令我心有戚戚焉或常想猛击一掌的句子和段落,委实甚多。只要你不断阅读佩索阿,你会发现他博大无限的感知。博尔赫斯的小说《沙之书》,里面讲到一本读不完的书,页与页之间总还有其他的页,无穷无尽,最后作家将它藏在了90万册图书中。对我来说,《惶然录》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,什么时候阅读都会像初次阅读那样,字里行间总有新的空地浮现出来。
梭罗曾说:“一个人可以从小地方意识到伟大的存在。”读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,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。这个在隐秘的角落度过短暂一生的思想者,用他诗性的语辞,带领读者通向澄明之境,那里没有绝望、愤怒、怨怼、诅咒,只有无上的欣喜和这种欣喜带来的不安与惶然。最后,我还是想用开篇的这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:“有时候,我认为我永远也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。一旦写下这句话,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谶言。”
是的,写下就是永恒。且让我们静静地翻开《惶然录》,读一读永恒的佩索阿。


